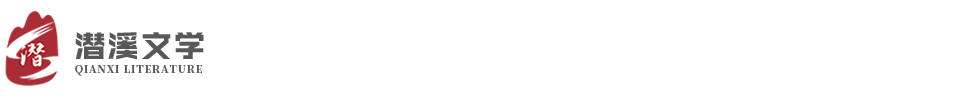|
|
编者按 诗不可解。 悲怛者,“顾惟蝼蚁辈,但自求其穴” 理想者,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 赤诚者,“假如我是一只鸟,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 反叛者,“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/ 谁期待,谁就是罪人” …… 这些诗,也无需解。 诗人用诗歌去关注、干预时代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,当短浅与世俗成为时代主流时,他们在触摸怎样的世界?那些隐含在汉字背后的公共情怀与理想,还能否被人们借来作一盏夜灯? 诗歌在悲吟、呼唤、呐喊的同时,政府与商业之外,公益行业正在一次次探索中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办法,同样要实现或近或远的公共理想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以“诗人如何看公益”为主题,专访了三位风格迥异的诗人。此为之一。 朵渔,原名高照亮,1973年生于山东。 在许多人眼中,朵渔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有社会意识的诗人之一。余秀华评价朵渔:“朵渔是我以为的中国诗人里最有担当,最有骨气的人。他的诗歌在现代的诗群里唯独发出黄金一般的色彩。中国诗歌写到现在,语言没问题了,手法没问题了,但是问题却越来越严重:没有思想了,沉不下去了,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,没有个性了。幸亏有朵渔,让我觉得作为诗人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的荣耀。” 最后的雪 朵渔 一冬无雪,仿佛悲哀没个尽头 春天临近,一场大雪为我们浮一大白 只有雪是免费的,希望雪不要落在 坏人的屋顶上,要落就落在鸽子的眼睛里 看,时代的清洁工又开始扫雪 要为我们扫出一条黑暗的通道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曾经说,价值观是诗歌要解决的终极问题。你认为诗歌写作应该遵循怎样的价值观?这是否也影响了你的诗歌中对现实社会的表达? 朵渔:我为什么一直说我们的主要问题还是价值观问题?因为价值观是基础,是大地,我们是在相似的基础和大地上写作的,如此才可以沟通和交流,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体。如果说“你写的是诗,那我写的就不是诗”,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共同体。现在的问题是,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基于价值观意义上的诗人共同体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同,人生观可能还更多和个体有关,价值观更具有公共性,解决的是诗歌公共性的一面。我们诗歌圈里吵吵嚷嚷这么多年,很多看似艺术之争或利益之争,事实上是价值观之争。你看重的,可能正是我所轻视的;你追求的,正是我所鄙弃的;你视之为黄金,我弃之如敝履。如此一个江湖生态,不打起来才怪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一直都有强烈的欲望去关注现实问题吗?在创作时,社会问题仍然会激起你强烈的表达欲吗?你认为用诗歌去关注、干预社会是种义务吗?你觉得当代诗人对社会议题的发声足够吗? 朵渔: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诗人就一定要去强烈关注现实,而是说,诗人要具有现实感。现实感是灵感的触角,是一种诗人自身就具备的天赋。没有现实感的诗人是难以为继的,因为现实感是大地,是人间性,是让诗意得以落实和生根的基础。一个有天赋的诗人,即便他不主动去关注现实,现实也会找上门来。 诗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,确有干预社会、对社会议题发声的义务,但诗歌本身没有这样的义务,诗歌能否为社会议题发声,端赖诗人的技艺和良心。我觉得当代诗人还是过于爱惜羽毛了,生怕自己的诗因对社会发声而变成“非诗”。没那么严重。 诗人至少可以在诗作之外去积极参与社会进程,这种自觉的承担会反过来作用于诗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,你写下了《今夜,写诗是轻浮的》,如果这些都如此无力,那我们又能去做什么? 朵渔:当我们自感软弱的时候,可能是我们坚强的开始。或者说当我们自感无用的时候,可能是我们常识感恢复的时候。如果每个人都能恢复自己的常识感,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愚昧了。软弱的个体也会增强团结感。哭泣是最有力的,哭泣让你抛弃幻觉,洗亮眼睛。 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干这种事情,它软弱、无用、无力,像人在神面前的感觉一样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文字是轻贱的,除非它让读者生出力量。但这已不是诗歌的时代了,读诗的人越来越少,当然也就无法找到诗里面的力量。你觉得是人们找到了其他的力量来源,还是诗歌出了问题? 朵渔:文字就是我们自己,轻贱文字的时候就是在轻贱我们自己。 诗也是很骄傲的,它永远不甘于为它的时代所用,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诗的时代。诗可能不会给人带来力量,也许更多的是让人感到无力,感到渺小和谦卑。读诗的人越来越少,这不是诗的损失,是读者的损失。 诗不是那么便宜,不是那么实用,不是那么会讨好人,它甚至会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诗这个东西,是在你喝酒吃肉之余的东西,如果你只是满足于喝酒吃肉,诗当然是多余的。因此说,诗歌并没出问题,读者也没出问题,各自的错位乃是诗之宿命。 卿本佳人,读不读都没关系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对于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时候,让你无力的时候,你如何调节自己去面对?你需要“振作自己”吗? 朵渔:就是要时常警告自己,当你“看开”一切、“放下”一切的时候,可能就是你迈入老迈和腐朽的时候了。而这也正是你年轻时最瞧不起的。因此要永怀希望,希望在,力量就在。这其中,找到希望所在最为关键,而不能只是盯着黑暗不放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提到,自己越来越关注“信”,如果写作没有一种终极的信靠,写作就是一种虚无的行为,最终也是无价值、无意义的。你找到的写作的信靠是什么? 朵渔:最近两年,更多在思考作诗之于人意味着什么。循此思路,又发现人之为人也是个难题。我们尚不懂“人”为何,我们尚缺乏“人”的形象与尺度。人如果只以自己为尺度,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形象,犹如不知死焉知生。我们缺乏一个作为尺度的“神”的形象。 荷尔德林诗里讲得很清楚,“神本是人的尺度”,在此基础上,“人是神的形象”。因为有一个神的尺度和形象,作为必有一死的人才得以被整全地认识。以前我只认识到人的悲苦无告,因此需要一个向其吁求的上帝。现在我知道,人是不可能自我整全的,人是有限的,人生而有罪,认识到自己的罪责是一个人前行的动力,敬畏上帝则是智慧的开端。以前我只认识到人之黑暗无穷的欲望,但很难对这种原欲/原罪展开真正的批判,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审判者,如果没有一个圣灵居于心中,人就不可能真正批判自己,也不可能有真实的道德生活,只会自我称义,或者陷入伪善。“神本是人的尺度”,我是从认识上帝开始理解荷尔德林这句诗的。这不仅是一种观念秩序的自我更新,同时也是一种诗学的更新。人如果失去了尺度,必有一死本身就是个悲剧。在此基础上,诗意味着什么?人有限,人又要言说;人“在世界中”,如何认识和道说“世界之外”的真理?只有依靠上帝的话语启示。而诗试图言说那不可言说的东西,那沉默的部分正与上帝的话语重合。这是一个奇迹——如果没有这个尺度,就无法进入那沉默的部分。如海德格尔所说的,人以神性来度量自身,“这种度量一旦发生,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。”人作诗,并以此获取一种“神性的形象”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觉得对投身公益的人来说,他们的终极信靠是什么?你认为什么样的人会乐于进入公益行业?对于社会问题,诗歌更多是在提出问题,去追问、呐喊,而公益人是在寻找和尝试具体的解决办法,你如何看待两者分别发挥的作用,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? 朵渔:终极而言,只有上帝是公益的。人有罪,人有限,人无法自我整全自我成圣。认识到人的有限性,然后投身到公益中,这不是对自我的荣耀,这是对神的荣耀。这和写作是一样的,写作首先是一种自我的救赎,当它对其他心灵产生影响,一种公益性便在其中了。 公益事业也不见得是直接去解决问题,它也可以旁敲侧击,它是建设者也是批评者。我觉得公益事业也是件久久为功的事,需要慢慢发酵,才能显示其功用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是乡村儿童诗歌教育公益机构“是光”的理事,当时是什么契机?参与“是光”的活动之后感受如何? 朵渔:当时我凑巧也在做一个儿童诗歌普及公益活动,叫“读诗吧,孩子”,和康瑜她们的“是光”有些相似之处,于是就有些合作。我是觉得康瑜她们作为“90后”的大学生,没出校门就开始做公益,我是很兴奋的,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这样做的。能够为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对我也是一种荣幸,我觉得是她们这些年轻人带着我这个老家伙在做些有价值的事情,我很感谢她们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同时也在诗歌阅读推广公益平台“诗歌阅读馆”担任导师。做这么多诗歌公益教育工作,内心的动力更多来自对诗歌的爱还是做公益的满足感?你如何看待公益对国内诗歌教育发展的作用? 朵渔:首先,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下,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,恰巧儿童诗歌教育是无害的,是被允许的;其次,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,能用自己的专业去服务有限的人,为什么不去做呢?我们现在的诗歌教育还没有形成专业的模式,公益行动功效甚微,但做一点就比不做强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至少在公益界,主流观点认为政府、商业、公益这三者不可或缺,公益,很多时候代表着整个第三部门,三者需要相互支撑来调节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,但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显然是严重滞后的。对国内公益现状,你有怎样的观感?你是否也看到一些问题? 朵渔:现在,公益的大环境依然是谨小慎微的,发展到什么程度,都在政府的拿捏之下。商业的参与让人欣慰,形成文化尚需时日,对其中的投机性我们也暂不去猜测。公益组织要形成第三种力量,任重道远,其本身依然要解决自己的价值观、运行模式和商业信誉问题,一旦信誉崩塌,公益将万劫不复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对近几十年汉语诗歌变化的观察是,由个人英雄情结挣脱出来一个个正常的人。而国内公益发展的一个趋势是,十几年前,公益的理想主义色彩更浓,现在则是越来越多不同的人涌入公益领域,且他们谈论的不止于单纯的善,也会有效率、回报等等。你认为这两种变化是否存在某种相似性?其背后是不是都和社会发展与演变存在某种联系? 朵渔:公益活动最初的理想主义,强调的是价值观;公益要发展,离不开成熟的运行模式,这其中必然涉及效率、回报等等商业问题,这是公益自身成熟的表现。但公益事业不是冷冰冰的商业运行模式,至少就其对公众所展现的商业信誉而言,它依然离不开对价值观的依赖。价值观——模式——商誉,三者缺一不可,互相依存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生活中是否也接受过公益服务?感受如何?你接触和关注过很多公益项目,总体感受如何?你认为这些项目的质量如何?透明度和可信度呢? 朵渔:我接受过一些志愿者服务,有些感觉还好,但大多数感觉浮夸、低效,这并非志愿者的问题,主要是组织方的问题,比如用公益来做秀等等。这些表面的浮夸会败坏公益的形象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生活中你是一个经常做公益的人吗?什么样的公益项目可以吸引你参与?如果选择公益机构捐赠或支持,你会选择哪一类型的公益机构,有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,已经很知名的公益组织,还是默默无闻的草根机构? 朵渔:我应该是参与公益比较多的了,也了解其中的甘苦、喜悦与幻灭感。参与公益是一项有限的施予,自我的收获可能更大。 于社会而言,公益是一项有益的补充,也是一种温柔的反抗,能否发展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,端赖政府的拿捏度,以及公益组织自身不要出问题。 (来源:社会创新家) |